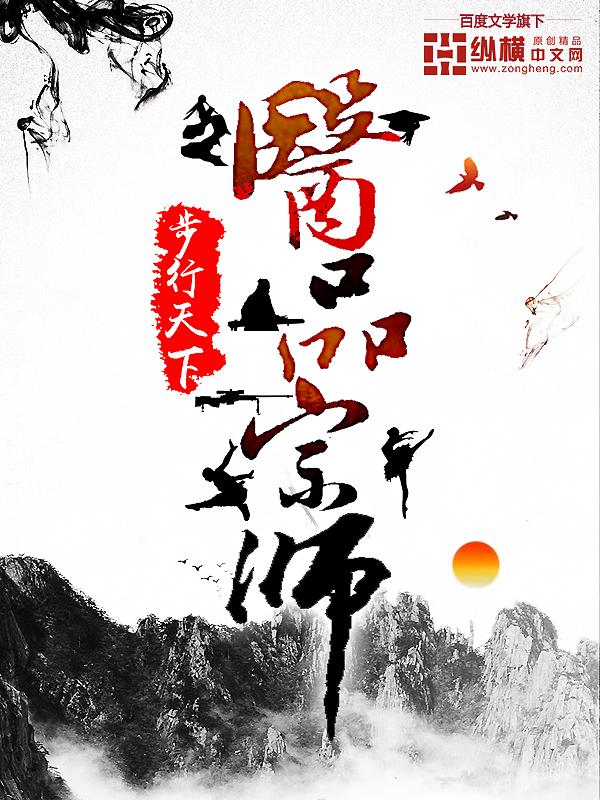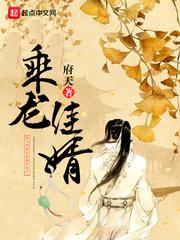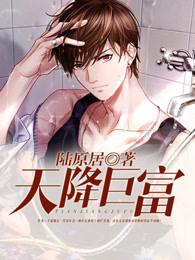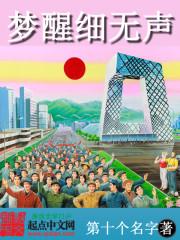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611章 施家祠堂(第1页)
第611章施家祠堂
第六二六章施家祠堂
另外,林啸还存了一个小心思。
对这首批受训的三百人,他还有一个额外的期待——培养若干基层干部。
毕竟,白驹场只是弹丸之地,整个两淮地区,还有那么多的盐场尚未接管,盐业生产基本瘫痪,盐民的生计问题很大,要解决这一切,急需大量的人手。
然而,林啸自忖在此滞留的时间有限,手头又无足够的部队,所以,他决定另辟蹊径,利用“盐场团”,将这两项工作合二为一,争取在短时间内,培养出一批半军事化的基层干部,逐批派驻各地。
林啸的目光,就落在了这首批人员的身上,他们是培养重点,既要训练军事,又要培训一些地方工作的常识。
他的这个思路,同样也来自于后世经验的启发。
在后世,抗战时期,活跃于游击区的“武工队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即使全国解放后,农村的基层干部,也有许多来自于退伍军人,这个做法,是有一定成效的。
因此,为了兼顾日常劳动和军事训练,他决定采用全员轮训与少量特训相结合的方式,在此基础上,轮流担负一些常备任务。
在他的设想里,整支民工队,最终要做到全民皆兵,从中不断发现、选拔基层干部,为以后的大发展,预备下一些资源。
武器方面,除冷兵器外,应该额外配备一定数量的火器,最好是步枪,军工进度跟不上的话,哪怕燧发枪也行。
不过,林啸担心,这件事真正实施起来,困难不小。
首先,这个“盐场团”,为什么是半兵半民的性质,为什么既要生产,又要兼顾剿匪和治安,要跟民工兄弟们解释清楚。
其次,即便思想工作做通了,他们八成会要求提高待遇,对这一点,要有所准备,设法解决。
因为,无论民工还是盐民,他们的思想是朴素的,对自己理解不了的事物,通常会很迷惑,会抱有怀疑的态度。
在他们的认知里,大明朝的规矩,“兵”就是军籍,“民”就是民籍,是含糊不得的。
应征当兵,说白了就是拿脑袋搏前程,用性命换钱财;而民户,就是在田地上卖力气,他们的活法很简单,就是向土地要活路,给官府交赋税。
要他们干士兵的活,接受部队那般的管理和训练,却不给当兵的待遇,这是说不通的。
毕竟,讨虏军战士每月五两的军饷,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,而他们作为随军民工,如今又成了盐场工人,每月两吊钱(合铜钱两千文,相当于碎银二两)的工钱,是写在了契约里头的。
老实说,能拿两吊钱,他们本来已经非常满意了,这从他们的工作热情上可以看出来。
可如今,这个“半兵半民”,是啥玩意儿?
这个新身份,到底算不算从军打仗,是不是应该涨工钱?
“这个问题不能敷衍,”
林啸蹙眉沉思,“只有充分尊重他们的诉求,尽量给予满足,他们才能支持你,心甘情愿地听从你的指令行事。”
“每月再增加一两,应该差不多了,”
他默算着,“毕竟,他们终究能想明白,剿匪,跟直面鞑子的骑兵,完全是两码事。”
“五千人,每人增加一两,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”
他用力揉了揉太阳穴,感觉头都大了。
另外,还有一个困难,就是文化程度问题——即便那三百人中,还有近半是文盲。
在这个时空,如果仅仅当一个普通军人,不识字的问题倒还不算太大,但是,作为未来的基层干部,如果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,就不大合适了
林啸苦思冥想,越想越多,越想越头疼,训练大纲几乎写了一整夜,直到东方发白的时候,他才倒在行军床上,和衣而睡。
第二天一早,帐篷外鼎沸的人声就把他吵醒了——勤劳的民工们,已经在出工了。
他一骨碌爬起身,用力摇了摇脑袋,感觉晕晕乎乎的。
“司徒正!”
他习惯性地大喊,“司徒正!”
“报告首长!”
一名全副武装的小战士闻声跑了进来,报告道,“大队长去村里了!”
“哦?”
林啸迷迷瞪瞪地点点头。
医品宗师
他是武林中最年轻的武学宗师,拥有神秘的绝对手感,可他现在却是一名普通的中医大学的大一新生,本想低调的学学医,看看病,恋恋爱,可在一次中秋晚会被迫表演中震惊了全场,注定闪耀的美好大学生活从此开始了...
乘龙佳婿
穿越三年,长在乡间,有母无父,不见大千。就在张寿安心种田教书的时候,有一天,一队车马造访,给他带来了一个未婚妻。当清俊闲雅的温厚乡下小郎君遭遇美艳任性的颜控千金大小姐,鸡飞狗跳的故事开始了。...
财运天降
陆原语录作为一个超级富二代装穷是一种什么体验?别拦着我,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!...
最后一个使徒
黄沙掩埋了白骨,夕阳下的风中,有着血腥的味道。大陆的痛楚,在朝着四面八方扩散,当大爆炸的历史出现拐点的时候,当巨大的钢铁要塞横亘而过,遮蔽住人们视野的时候...
梦醒细无声
由终点回到原点,洪涛又回到了他第一次重生前的时代,不过失去了三次重生穿越的所有记忆。假如没有重生过,没有记忆的金手指,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?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高潮期,他是屹立在潮头的弄潮儿?还是被浪潮拍碎的浪花?他的记忆还能不能回来?江竹意还会不会伴着他这一生?金月在这一世里和他又有什么交集?小舅舅还会是那个妻管...
诸天至尊
十方地狱禁不了我魂,浩瀚星空亮不过我眼,无垠大地载不起我脚,诸天神魔承不住我怒!我要这天地匍匐,我要这轮回断灭!...